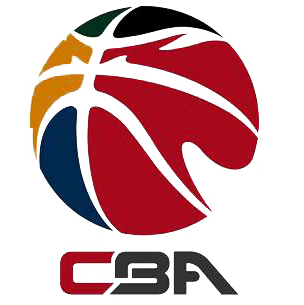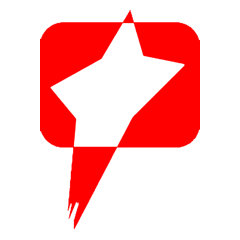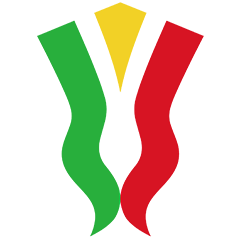2022年5月,英國女雙名將塔拉·摩爾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站賽事中被檢出諾龍與勃地酮陽性,隨即遭到臨時禁賽。2023年12月,獨立法庭認定其陽性結果源于污染肉類,裁定她“不存在過錯或疏忽”,摩爾得以在2024年4月復出。然而,近日國際網球誠信機構(ITIA)的上訴被體育仲裁法庭(CAS)支持,摩爾被改判四年禁賽,扣除已執(zhí)行的19個月臨時禁賽后,她最早需等到2028年才能重返賽場,屆時36歲的她,職業(yè)生涯恐將終結。

CAS在裁決中稱,摩爾“未能證明樣本中諾龍濃度與食用污染肉類的情況相符”,且無法證實違規(guī)行為“非故意”。這一結論與獨立法庭的判決截然相反,暴露出反興奮劑體系中科學證據采信標準的模糊性:
1. 肉類污染類爭議:類似案件中,運動員常以肉類污染為由申訴,但裁決結果差異顯著。ITIA稱本案諾龍濃度異常高,卻未明確界定合理范圍。
2. 舉證責任倒置:根據《世界反興奮劑條例》,運動員需自證“無過錯”,但污染源追溯本就困難,邊緣選手更缺乏資源聘請頂級專家團隊。摩爾案中,獨立法庭曾接受其證據,CAS卻推翻結論,凸顯裁決的主觀性。

本案引發(fā)對反興奮劑執(zhí)法一致性的質疑。對比近年案例:
辛納案:意大利新星兩次藥檢陽性,但迅速與ITIA達成和解,僅缺席賽場三個月。
斯瓦泰克爭議:興奮劑檢測陽性后被禁賽一個月,而且解禁后才公之于眾。
而摩爾作為雙打選手,收入微薄,卻遭頂格處罰。這種差異折射出體育司法中資源與話語權的不平等:明星選手可通過快速和解減輕影響,而邊緣運動員往往被動承受制度性風險。

摩爾案揭示了反興奮劑體系的深層問題:
1. 維權成本高昂:長達19個月的調查與訴訟消耗了運動員的黃金運動生涯,而CAS裁決“幾乎不可推翻”的特性,使申訴淪為形式。
2. 科學評估不透明:ITIA依賴“獨立科學顧問”的結論,但具體評估標準未公開,運動員難以針對性抗辯。
3. 處罰與過錯失衡:即便接受污染解釋,四年禁賽的懲罰是否合乎比例原則?

對此公眾強烈呼吁國際體育仲裁亟需系統(tǒng)性改進:
1、統(tǒng)一科學證據標準:建立公開的污染物濃度閾值指南,減少裁決任意性。
2、降低運動員舉證難度:在污染誤服案例中,反興奮劑機構應承擔更多舉證責任。
3、審查處罰一致性:設立獨立監(jiān)督機構,評估同類案件的裁量尺度,避免“因人而異”。

塔拉·摩爾的遭遇并非孤例,而是反興奮劑體系結構性缺陷的縮影。當規(guī)則執(zhí)行淪為“幸存者游戲”,體育公平的核心價值便遭侵蝕。若制度無法保障“無過錯者”免于重罰,那么維護純潔性的初衷,反而可能成為摧毀運動員的利器。(來源:網球之家 作者:Mei )

 精品閱讀
精品閱讀